2005 年 11 月 13 日

最近第二次去法國,上次去是跟一群好朋友去發表論文,時間大概是2000年左右?五年之後舊地重遊,一樣的奧賽美術館、一樣的羅浮宮,感覺不同許多。
五年前還算是學生身份的我,所謂的行李箱不過是個大型登山背包,不管坐飛機、公車、地鐵,轉換地點就像是行動力極強的游擊隊,只要有設計精良的雙肩背帶,似乎什麼都可以扛在背上,走到哪,背包就能擺到哪,不管是有尿騷味的地鐵,或者是體面的機場候機室。全部的行李不過是吸汗的內衣、輕便的服裝以及筆記本,皮鞋是沒有的、襯衫是沒有的、連數位相機也是沒有的。這樣的裝束進到博物館,就像是不修邊幅的年輕人,在知名的藝術品前竭盡腦汁去體會感受,想像回到那樣的世界,感受作品散發的卓越風華。但旁人看來,畢竟有些怪異。
五年後經過簡短社會訓練的我,所謂的行李箱雖不追求名牌,但也是著重實用品質的 Samsonite,有輪子、有提把、能上鎖,上飛機自然是托運的,住的飯店星等也比上回多出一倍,從兩顆到四顆星。全身從上到下分別是 G2000 的襯衫與褲子、Nike 黑襪、以及阿瘦皮鞋。隨身帶著的相機是 Canon 早期的 DSLR D60,還有顆外閃跟定光圈鏡。行動力是受限的,因為優雅變成中心德目之一,小資產階級的生活習性與我融為一體。我不再像以前,在博物館走累了,能夠不顧旁人的在名畫前坐下,眼睛不停盯住想看的作品,在疲倦時,能選擇的就是花兩塊多歐元到咖啡廳去坐下聊天。五年前重視我看到什麼、吸收什麼,五年後我在意的是某種優雅與身為中產階級觀光客在博物館中的表演,甚或有所體悟這層表演有著亞洲人觀光客與法國本地人的辯證在。
其實我不是那麼有能力抵抗環境的人,進到工作的場合,也不太適合再穿牛仔褲、T-shirt和籃球鞋,於是乎隨意買點看起來像是跟大家一樣的襯衫、西裝褲、皮鞋,變成是一種偽裝,告訴大家:「小弟我沒那麼離經叛道,跟大家一樣,看場合做事情」,似乎是對這整個文化的輸誠與效忠,讓自己在生活上順利點就是。如果今天我生活在一個需要手拿小冊子常常念些偉人講的話的民族國家,大概我也是會做一樣事情的那種人。相對的,若是我活在一年放假超過 150 天,生活充滿咖啡跟香水的國家,一定也是從眾的。
這種體悟,有點無奈,卻也還能自嘲。學生時代,總把主義之類的東西看的很重,覺得思想決定行動,立場是一個人與眾不同的關鍵,需要從內而外徹底的去實踐才值得尊敬。長大了,知道自己的斤兩,遇過挫折、疾病、中產階級的快樂生活,棍子蘿蔔夾擊之下,我想我還是隨波逐流的好。
倒也不是全面撤守吧,還是有些小小的夢想、小小的堅持,在仍有餘欲的狀況下希望能維持住。對病人的負責、對工作的堅持、對自我的要求。只不過,當事情不見得能如自己的意時,更懂得看開、轉個念頭、甚或放手。這是這五年來不太起眼的小小改變。
若是五年後我再去法國,會是怎樣的光景呢?會寫出怎樣的文章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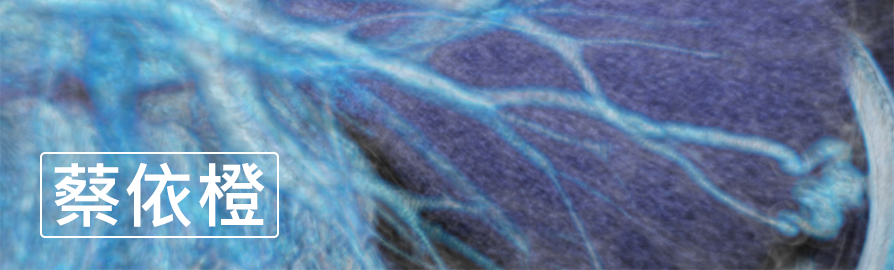
第二次去法國
2005 年 11 月 13 日
最近第二次去法國,上次去是跟一群好朋友去發表論文,時間大概是2000年左右?五年之後舊地重遊,一樣的奧賽美術館、一樣的羅浮宮,感覺不同許多。
五年前還算是學生身份的我,所謂的行李箱不過是個大型登山背包,不管坐飛機、公車、地鐵,轉換地點就像是行動力極強的游擊隊,只要有設計精良的雙肩背帶,似乎什麼都可以扛在背上,走到哪,背包就能擺到哪,不管是有尿騷味的地鐵,或者是體面的機場候機室。全部的行李不過是吸汗的內衣、輕便的服裝以及筆記本,皮鞋是沒有的、襯衫是沒有的、連數位相機也是沒有的。這樣的裝束進到博物館,就像是不修邊幅的年輕人,在知名的藝術品前竭盡腦汁去體會感受,想像回到那樣的世界,感受作品散發的卓越風華。但旁人看來,畢竟有些怪異。
五年後經過簡短社會訓練的我,所謂的行李箱雖不追求名牌,但也是著重實用品質的 Samsonite,有輪子、有提把、能上鎖,上飛機自然是托運的,住的飯店星等也比上回多出一倍,從兩顆到四顆星。全身從上到下分別是 G2000 的襯衫與褲子、Nike 黑襪、以及阿瘦皮鞋。隨身帶著的相機是 Canon 早期的 DSLR D60,還有顆外閃跟定光圈鏡。行動力是受限的,因為優雅變成中心德目之一,小資產階級的生活習性與我融為一體。我不再像以前,在博物館走累了,能夠不顧旁人的在名畫前坐下,眼睛不停盯住想看的作品,在疲倦時,能選擇的就是花兩塊多歐元到咖啡廳去坐下聊天。五年前重視我看到什麼、吸收什麼,五年後我在意的是某種優雅與身為中產階級觀光客在博物館中的表演,甚或有所體悟這層表演有著亞洲人觀光客與法國本地人的辯證在。
其實我不是那麼有能力抵抗環境的人,進到工作的場合,也不太適合再穿牛仔褲、T-shirt和籃球鞋,於是乎隨意買點看起來像是跟大家一樣的襯衫、西裝褲、皮鞋,變成是一種偽裝,告訴大家:「小弟我沒那麼離經叛道,跟大家一樣,看場合做事情」,似乎是對這整個文化的輸誠與效忠,讓自己在生活上順利點就是。如果今天我生活在一個需要手拿小冊子常常念些偉人講的話的民族國家,大概我也是會做一樣事情的那種人。相對的,若是我活在一年放假超過 150 天,生活充滿咖啡跟香水的國家,一定也是從眾的。
這種體悟,有點無奈,卻也還能自嘲。學生時代,總把主義之類的東西看的很重,覺得思想決定行動,立場是一個人與眾不同的關鍵,需要從內而外徹底的去實踐才值得尊敬。長大了,知道自己的斤兩,遇過挫折、疾病、中產階級的快樂生活,棍子蘿蔔夾擊之下,我想我還是隨波逐流的好。
倒也不是全面撤守吧,還是有些小小的夢想、小小的堅持,在仍有餘欲的狀況下希望能維持住。對病人的負責、對工作的堅持、對自我的要求。只不過,當事情不見得能如自己的意時,更懂得看開、轉個念頭、甚或放手。這是這五年來不太起眼的小小改變。
若是五年後我再去法國,會是怎樣的光景呢?會寫出怎樣的文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