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 年 01 月 22 日
對真假生死等等的對立面,有點感想,從最近看的書開始說起好了。
最近在看新田次郎的武田信玄,同樣是寫戰國,新田次郎的筆鋒跟山岡莊八的差異就不小,新田次郎不避諱的把小說與歷史的界線劃的很清楚,也把自己定位在小說層次,所以他幫一些沒有名字的女性加上名字,把傳說中的戰役描寫得歷歷在目,在小說之餘,並引用既有的文獻作註腳,小說與歷史的辯證於是清楚。山岡莊八則或許採取另一種態度,將自己的歷史小說定位在還原史實以及教育傳承,主觀投入的感情較少,或者該說刻意的將小說的氣氛壓低,將歷史與小說合而為一,所以一般對山岡莊八的小說總是評價為入門第一本,兼顧故事性與史實的絕佳平衡。
戰國畢竟離現在太遠,可得文獻較少,自然很難還原歷史現場,但即使流傳下來的書,也不乏甲陽軍鑑這樣明史書暗小說備受攻擊的文本,依據新田次郎描述,這本書在歷史界的評價並不高,由於作者是武田臣山本戡助的兒子,為了美化自己的父親,將之重新描寫為武田信玄的軍師,對於某些特定史實,扭曲改寫的也很多。那麼,什麼是真,什麼是假?近的人說的真,遠的人說的假?還是既然都是人,免不了不能全真。
同樣一個故事,不同的作者便會有不同的處理方式,著重的重點也不同,但很明顯的,「真相只有一個」,這是名偵探江戶川柯南告訴我們的事情,那麼,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似乎是這樣的:史實只存在一個客觀虛擬的公正角色的心中,在歷史現場的每個人,對於「真實」的詮釋又有所不同,這個不同則源自於態度、角色、成見、立場或期許,等等不同的情緒體驗。幾百年後,就如口耳相傳的故事一樣,與其說是回顧歷史,這些口述文本代表的其實更是曾經傳遞過這些話語的人們的共同意識。或許反應一個努力就能出人頭地的平民關白觀點,或許反應一個暴政必亡仁政得天下的看法,到底我們在看歷史,還是在看當今日本作家寄託於戰國故事想要告訴我們的事情?
另一件有趣的事情,是有關生死的大事,武田信玄、德川家康都曾經衝動過,在年輕時,只看到戰爭勝利的榮耀,一味的只想向前衝,因此信玄失去了板桓信方、甘利虎泰兩員大將,德川則在三方原幾乎全滅,但聰明人畢竟是聰明人,隨著歲月的增長,很快的重新定義戰爭,從「戰,而後求勝」到「先勝,而後求戰」,於是中晚年的戰爭幾乎以謀略為主,勝率也直線提高。到這就不得不佩服豐臣秀吉,或許年輕時代可支配資源的有限,苦日子的訓練讓他能比別人更早的理解到戰爭的本質,於是乎從墨俁築城開始,幾乎所有的戰爭都是巧思,工事、人心、謀略、技策,真正是全面化的戰爭。晚年的德川幾乎是到了哲學家的地步,對於生死、永恆、和平有著超越世俗的看法,能與這樣的人物對談,想必該是很棒的心靈洗禮。他對於生死怎麼看呢?
恰好是在醫療界這樣一個可以在很年輕就大量的看到生死的修練場,我從20歲還在學校到現在這八年間,在人生觀與思考上幾乎變成了兩個人,畢竟每天衝擊的事情都太多太大,如不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思考體系,恐怕會走向工作機器或者心智崩潰兩條路。舉幾個簡單的例子,一樣28歲,我在做血管拴塞治療癌症,躺著的就是一樣年紀的年輕女生,得了少見、靠近心臟的平滑肌肉瘤,我會自問,到底是誰決定誰要生病誰是健康的呢?我沒有生這樣的重病,就只是因為幸運嗎?也有比我稍長,剛結婚的男性病人,大腸癌末期,輸尿管被壓迫,兩側腎臟插管,每三個月都要來換一次,也就意味著要痛一次,幸運的是,聊天之餘發現他有一個好老婆,沒有離開他,反倒是撐起一個家,並每天晚上幫他換傷口的藥。還有每天上班遇得到的同事,忽然一天發現癌症末期,半年內就走了。有些人會將這樣的差異歸因於上天給的試煉、前輩子修行的差異、命的輕重、業障等等,我沒有宗教,也沒有自成一格的超自然解釋,所以我依然迷惑。病人問我,我總是那一句台語:「一人一種命(幾郎幾寬命)」
有一陣子很嚮往僧侶那樣的生活,安詳的日子,在簡單反覆的生活步調中思索生命,但最近也想,沒有生命的衝擊,如何思考生命本身?若不是在這樣的工作環境執著著,或許我沒有機會經歷這樣的思考與成長,所謂大隱隱於市,大概有點這樣的味道。在生死繁忙的大市集,才更有機會思考生死,甚或超脫生死的執著。總有些執著、總有些看破,這樣的人生,也頂有趣。禮拜一到五極端忙碌,在六日值班時對著自己的電腦打打字,思考三十歲前的自己,這樣的人生也是不錯。既然活著,就好好享受生命帶來的喜怒哀樂,當成課題一樣的一一回應。
於是乎,什麼是真、什麼是假,什麼是生、什麼是死?那個是對那個是錯哪個是好那個是壞,似乎又有了另一層的混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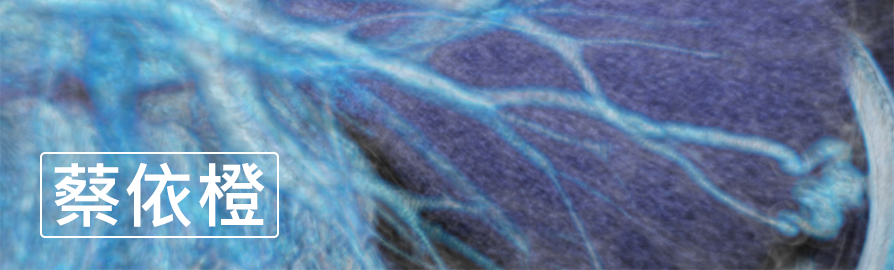
有關真假與生死 從武田信玄的小說說起
2006 年 01 月 22 日
對真假生死等等的對立面,有點感想,從最近看的書開始說起好了。
最近在看新田次郎的武田信玄,同樣是寫戰國,新田次郎的筆鋒跟山岡莊八的差異就不小,新田次郎不避諱的把小說與歷史的界線劃的很清楚,也把自己定位在小說層次,所以他幫一些沒有名字的女性加上名字,把傳說中的戰役描寫得歷歷在目,在小說之餘,並引用既有的文獻作註腳,小說與歷史的辯證於是清楚。山岡莊八則或許採取另一種態度,將自己的歷史小說定位在還原史實以及教育傳承,主觀投入的感情較少,或者該說刻意的將小說的氣氛壓低,將歷史與小說合而為一,所以一般對山岡莊八的小說總是評價為入門第一本,兼顧故事性與史實的絕佳平衡。
戰國畢竟離現在太遠,可得文獻較少,自然很難還原歷史現場,但即使流傳下來的書,也不乏甲陽軍鑑這樣明史書暗小說備受攻擊的文本,依據新田次郎描述,這本書在歷史界的評價並不高,由於作者是武田臣山本戡助的兒子,為了美化自己的父親,將之重新描寫為武田信玄的軍師,對於某些特定史實,扭曲改寫的也很多。那麼,什麼是真,什麼是假?近的人說的真,遠的人說的假?還是既然都是人,免不了不能全真。
同樣一個故事,不同的作者便會有不同的處理方式,著重的重點也不同,但很明顯的,「真相只有一個」,這是名偵探江戶川柯南告訴我們的事情,那麼,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似乎是這樣的:史實只存在一個客觀虛擬的公正角色的心中,在歷史現場的每個人,對於「真實」的詮釋又有所不同,這個不同則源自於態度、角色、成見、立場或期許,等等不同的情緒體驗。幾百年後,就如口耳相傳的故事一樣,與其說是回顧歷史,這些口述文本代表的其實更是曾經傳遞過這些話語的人們的共同意識。或許反應一個努力就能出人頭地的平民關白觀點,或許反應一個暴政必亡仁政得天下的看法,到底我們在看歷史,還是在看當今日本作家寄託於戰國故事想要告訴我們的事情?
另一件有趣的事情,是有關生死的大事,武田信玄、德川家康都曾經衝動過,在年輕時,只看到戰爭勝利的榮耀,一味的只想向前衝,因此信玄失去了板桓信方、甘利虎泰兩員大將,德川則在三方原幾乎全滅,但聰明人畢竟是聰明人,隨著歲月的增長,很快的重新定義戰爭,從「戰,而後求勝」到「先勝,而後求戰」,於是中晚年的戰爭幾乎以謀略為主,勝率也直線提高。到這就不得不佩服豐臣秀吉,或許年輕時代可支配資源的有限,苦日子的訓練讓他能比別人更早的理解到戰爭的本質,於是乎從墨俁築城開始,幾乎所有的戰爭都是巧思,工事、人心、謀略、技策,真正是全面化的戰爭。晚年的德川幾乎是到了哲學家的地步,對於生死、永恆、和平有著超越世俗的看法,能與這樣的人物對談,想必該是很棒的心靈洗禮。他對於生死怎麼看呢?
恰好是在醫療界這樣一個可以在很年輕就大量的看到生死的修練場,我從20歲還在學校到現在這八年間,在人生觀與思考上幾乎變成了兩個人,畢竟每天衝擊的事情都太多太大,如不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思考體系,恐怕會走向工作機器或者心智崩潰兩條路。舉幾個簡單的例子,一樣28歲,我在做血管拴塞治療癌症,躺著的就是一樣年紀的年輕女生,得了少見、靠近心臟的平滑肌肉瘤,我會自問,到底是誰決定誰要生病誰是健康的呢?我沒有生這樣的重病,就只是因為幸運嗎?也有比我稍長,剛結婚的男性病人,大腸癌末期,輸尿管被壓迫,兩側腎臟插管,每三個月都要來換一次,也就意味著要痛一次,幸運的是,聊天之餘發現他有一個好老婆,沒有離開他,反倒是撐起一個家,並每天晚上幫他換傷口的藥。還有每天上班遇得到的同事,忽然一天發現癌症末期,半年內就走了。有些人會將這樣的差異歸因於上天給的試煉、前輩子修行的差異、命的輕重、業障等等,我沒有宗教,也沒有自成一格的超自然解釋,所以我依然迷惑。病人問我,我總是那一句台語:「一人一種命(幾郎幾寬命)」
有一陣子很嚮往僧侶那樣的生活,安詳的日子,在簡單反覆的生活步調中思索生命,但最近也想,沒有生命的衝擊,如何思考生命本身?若不是在這樣的工作環境執著著,或許我沒有機會經歷這樣的思考與成長,所謂大隱隱於市,大概有點這樣的味道。在生死繁忙的大市集,才更有機會思考生死,甚或超脫生死的執著。總有些執著、總有些看破,這樣的人生,也頂有趣。禮拜一到五極端忙碌,在六日值班時對著自己的電腦打打字,思考三十歲前的自己,這樣的人生也是不錯。既然活著,就好好享受生命帶來的喜怒哀樂,當成課題一樣的一一回應。
於是乎,什麼是真、什麼是假,什麼是生、什麼是死?那個是對那個是錯哪個是好那個是壞,似乎又有了另一層的混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