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篇 WSJ 的文章採訪得很完整,但因為有付費牆,我將內容簡單整理如下,跟大家分享。
我想,曾經第一線面對過 SARS 的伙伴,很能感同身受。雖然,COVID-19 的 DDoS 更強上許多。
☞ Young Doctors Struggle to Treat Coronavirus Patients: ‘We Are Horrified and Scared’ / WSJ
這篇主要採訪紐約的住院醫師,由於疫情的緣故,整個紐約的醫療系統已經過飽和,人力嚴重不足,所以,只要你是住院醫師,不管哪一科,通通都被叫來顧病人。
狀況嚴重到,精神科的第一年住院醫師,就必須要去顧 ICU,而且要自己處理患者的診斷、治療,調整呼吸器!
第一年精神科住院醫師調整呼吸器?聽起來就好像會出事!的確,WSJ 記者拿到一些內部信件,年輕醫師一起跟醫院管理層反應,他們覺得壓力很大也很痛苦,想自殺。其中,有人承認自己把呼吸器設定調太高,患者沒多久就死了。
另一些年輕醫師則說,自己受不了這樣一週工作 90 小時,身兼主治醫師、護理師、呼吸治療師,還有清潔工。
主治醫師跟資深住院醫師,名義上都說有監督,但實際上根本沒辦法。而即使年輕醫師一個人顧 36 台呼吸器、90 個病人,他所需要的知識,都只能自己上網查。
以拍痰為例(敲打胸腔讓痰能排出),醫院只有提供 ZOOM 上課一次,然後兩頁的 Google Document,他們就要自己上了。
拍了半天,到底對不對還是有沒有用,也沒有人可以跟他們說。很多住院醫師只能趁空檔,去 YouTube 再自己搜尋,進修一下。
另一個住院醫師,遇到的 COVID-19 患者,也有腸胃道出血,而且 CBC 抽起來狀況很不好,於是他安排常規輸血。
但一個小時過後,主治醫師才終於忙完能來看,之後跟他說:「我們當初應該用更積極的方法輸,目前這樣不行。」然後患者就過世了……
(因為 WSJ 是寫給一般人看的,這裡推測 R 只給了一條 IV,但 VS 覺得 hypovolemic 了,應該好幾條 line 一起上,有什麼就輸什麼才來得及。)
因為工作壓力高、時間長,且在美國,住院醫師領的比基本工資沒高多少(這是真的,有在紐約工作的新思惟校友確認過,低到政府會寄信跟你說你可以申請房屋補助!),也沒有任何加班費,一部份的住院醫師,聯合寫信給醫院管理層要求加薪。
畢竟,他們認為自己承擔了額外的風險,也付出了額外的貢獻,遠超過自己原本的訓練計畫。
但醫院管理層回覆,比較委婉的是說,醫院的財務狀況已經相當不好,實在沒辦法給。
比較機車的則是回:我不是不能理解你的焦慮啦,不過,在危機時刻要求風險津貼,我看你對醫學可能沒什麼熱情,不太適合喔……
“I am not indifferent to your anxieties but personally feel demanding hazard pay is not becoming of a compassionate and caring physician.”
事實上,這群住院醫師也根本沒有討論勞動權利的籌碼,因為他們還需要考專科。
如果你跟醫院討價還價,結果被開除,或者自己辭職,沒能完成住院醫師訓練,這在履歷上就是個污點,日後不太會有醫院收,基本上醫療生涯幾乎是毀了。
護理師有工會保護,也受各種勞動條件規範。但住院醫師什麼都沒有。這也是為什麼住院醫師會被要求作那麼多工作的根本原因。
不過另一方面,也有一群住院醫師,很正向的看待這樣的機會,覺得能在這樣的危機時刻提供幫忙,是很值得驕傲的事情。
他們不管自己應徵的是哪一科,都自願前往 ICU,認真學習各種能救人的技術,並積極的填補任何體系需要的位置,認為這樣的學習機會,千載難逢。
即使在學校也沒看過人拍痰、設定呼吸器,但自己查資料、看影片、思考治療原理,然後馬上就能派上用場,真的看到患者康復,讓他們覺得很棒。
但是,由於 COVID-19 死亡的患者還是很多,最困難的,就是告知家屬死訊。
對一個年輕的住院醫師來說,還沒看過幾次主治醫師示範,就要自己打電話告知家屬:「你先生過世了,而且因為隔離,你不能來醫院,我們會把遺體送過去。」
然後,聽著家屬無助大哭,是很令人悲傷,且必須自己去體會承受的事。
閱讀筆記討論 / 新思惟之友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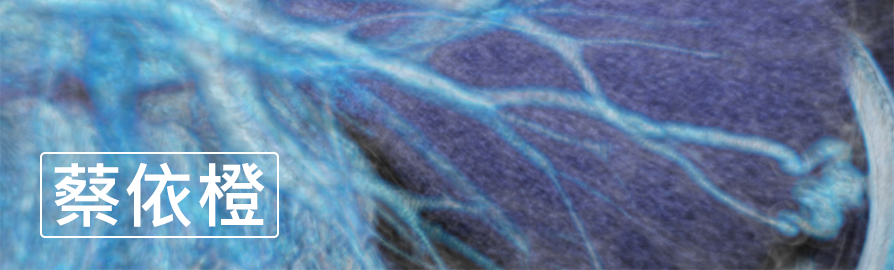
———- ———-
發問噗
如果戲稱醫學系公費生是國家的社畜,那政策有沒有必要
太開放的問題囧
不知所措
謝謝,不勝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