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 年 04 月 18 日
最近埋頭工作,有朋友問我,你這樣專心在工作上,不管世界發生什麼事情,連張錫銘是誰都不知道,甚至幾乎拋棄自己的健康在拼,之前又生過病,真的對嗎?值得嗎?
我想了想,忽然想通了。
生病對我,就像唯一也是最後一次爬玉山,走在將融的雪層卻沒有雪仗,只是穿著普通的布鞋,45度的山坡,滑下去就是幾百公尺了,找不到的。這兩次經驗是我最靠近死亡的時候。一次在山上,天未破曉,一次在我工作的醫院,兩個月靜止的過程。
如果說這些靠近死亡的經驗讓我學會什麼?或許不是怎麼去珍惜健康,卻是把每一天當成最後一天的過活,想作什麼、想完成什麼,就不留遺憾的努力。
在我生病的前一晚,我不知道自己將要生病,也是一樣的站在station寫病歷。既然這樣,我不把每天當成最後一天,怎麼知道當自己的文章登上國際期刊時,自己是在病房?還是在天堂?魯冰花的故事讓我很沒安全感,生病的過程更加確認。
焦土之春編者群邀我寫稿時,正是我完成近千例肝癌拴塞、投出第一篇國際論文被接受的那段時間,經過門診等候區,看到TVBS報導槍擊案、看到隔天藍綠的反應(我晚上沒有電視看的,只有白天經過公共區域時瞄一下),忽然就掉下眼淚來了,感覺這片土地上的人很不爭氣,上電視的那群更糟糕。
一直以來有個跟世界競爭的夢想,作大學生,作醫學生,作醫生,作學術研究,我的認同社群是一個我從來沒去過從來沒看過的國際社群。
也常想,台灣土地是小,但國民所得、關鍵技術、人口數,比起加拿大、德國、荷蘭不遑多讓,但整體競爭力就是很差,不成比例的差,專業不專業,政治卻凌駕一切。
作個暗殺的槍手,也可以更專業的。作個反對黨主席,也可以更專業的。作個醫生,也可以更專業的。作個國會議員,也可以更專業的。
專家是不是訓練有素的狗,我想也要看他所深處的社會,如果當整個社會的「人」,都泛政治化,都在意煽動、在意喧鬧,那麼專家真的是「狗」,他們只是一群笨蛋,服務著大眾罷了。
在這樣的世界,我反倒寧願當「狗」,至少狗的世界輕鬆多了,而且很多事情可以講道理,情緒也不會凌駕一切,反正就是開心迎接每一天。
所謂公民的責任不是跟著上街頭、叫囂、CALL IN而已。有些人選擇寧靜、冷漠、等待,等待一個平安祥和的討論場域,等待一個就事論事的公共論壇,等待即使有著相反意識型態的人們也能心平氣和的溝通彼此差異的一天。
在這天到來前,我繼續用我的方法關心我的國家,我繼續在專業上邁進國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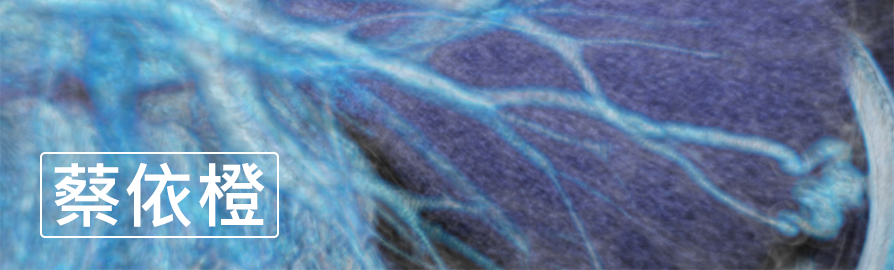
期許專業祥和的一天
2005 年 04 月 18 日
最近埋頭工作,有朋友問我,你這樣專心在工作上,不管世界發生什麼事情,連張錫銘是誰都不知道,甚至幾乎拋棄自己的健康在拼,之前又生過病,真的對嗎?值得嗎?
我想了想,忽然想通了。
生病對我,就像唯一也是最後一次爬玉山,走在將融的雪層卻沒有雪仗,只是穿著普通的布鞋,45度的山坡,滑下去就是幾百公尺了,找不到的。這兩次經驗是我最靠近死亡的時候。一次在山上,天未破曉,一次在我工作的醫院,兩個月靜止的過程。
如果說這些靠近死亡的經驗讓我學會什麼?或許不是怎麼去珍惜健康,卻是把每一天當成最後一天的過活,想作什麼、想完成什麼,就不留遺憾的努力。
在我生病的前一晚,我不知道自己將要生病,也是一樣的站在station寫病歷。既然這樣,我不把每天當成最後一天,怎麼知道當自己的文章登上國際期刊時,自己是在病房?還是在天堂?魯冰花的故事讓我很沒安全感,生病的過程更加確認。
焦土之春編者群邀我寫稿時,正是我完成近千例肝癌拴塞、投出第一篇國際論文被接受的那段時間,經過門診等候區,看到TVBS報導槍擊案、看到隔天藍綠的反應(我晚上沒有電視看的,只有白天經過公共區域時瞄一下),忽然就掉下眼淚來了,感覺這片土地上的人很不爭氣,上電視的那群更糟糕。
一直以來有個跟世界競爭的夢想,作大學生,作醫學生,作醫生,作學術研究,我的認同社群是一個我從來沒去過從來沒看過的國際社群。
也常想,台灣土地是小,但國民所得、關鍵技術、人口數,比起加拿大、德國、荷蘭不遑多讓,但整體競爭力就是很差,不成比例的差,專業不專業,政治卻凌駕一切。
作個暗殺的槍手,也可以更專業的。作個反對黨主席,也可以更專業的。作個醫生,也可以更專業的。作個國會議員,也可以更專業的。
專家是不是訓練有素的狗,我想也要看他所深處的社會,如果當整個社會的「人」,都泛政治化,都在意煽動、在意喧鬧,那麼專家真的是「狗」,他們只是一群笨蛋,服務著大眾罷了。
在這樣的世界,我反倒寧願當「狗」,至少狗的世界輕鬆多了,而且很多事情可以講道理,情緒也不會凌駕一切,反正就是開心迎接每一天。
所謂公民的責任不是跟著上街頭、叫囂、CALL IN而已。有些人選擇寧靜、冷漠、等待,等待一個平安祥和的討論場域,等待一個就事論事的公共論壇,等待即使有著相反意識型態的人們也能心平氣和的溝通彼此差異的一天。
在這天到來前,我繼續用我的方法關心我的國家,我繼續在專業上邁進國際。